女权主义视角下的生理/社会性别(三)
| 酷儿论坛翻译组
女性群体
关于社会性别/生理性别区别的评论往往对女性这一归类的可行性提出了质疑。女性主义运动的目标是终止整个女性群体受到的压迫。但是如果女性主义者们认同上述的观点,即社会性别的建构不该基于一个统一的标准,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严格区分开来是不合理或至少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而且性别特征会影响我们对女性的定义(这些性别特征并非单独必要或者充分联合,比如 ta 们的社会角色、职位、行为、特殊品质、身体特征和经历),那么我们该如何去理解“女性”这个群体呢?女性主义运动要想做到真正的包容,就必须要解决性别建构中包含的文化差异和社会差异,并且要格外注意不能让女性的共同特质掩盖了个体间的差异性。如琳达·阿尔科夫(Linda Alcoff)所说,以上的观点会导致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女性主义者们一边否认对“女性”的统一归类标准,一边以女性群体的名义提出政治要求(2006,152)。如果说我们不应该对“女性”有一个统一标准的归类,那么究竟是什么将女性团结在一起,我们又该怎样判断谁可以被称作女性,女性主义者们又能代表女性提出怎样的需求呢?
在政治方面,有很多因素证明了摒弃对女性归类的统一标准是不合理的(Alcoff 2006; Bach 2012; Benhabib 1992; Frye 1996; Haslanger 2000b; Heyes 2000; Martin 1994; Mikkola 2007; Stoljar 1995; Stone 2004; Tanesini 1996; Young 1997;Zack 2005)。例如,扬(Young)在文章中提到斯佩尔曼(Spelman)的说法:我们应该将女性从一个整体类别降为一个由大量个体组成的集合,并且没有任何足以定义这整个群体共同特征(1997,20)。黑人女性与白人女性是不同的,但是在这两个群体的成员在国际、种族、阶级、性取向和经济地位方面也各不相同。比如,富裕的白人女性与工薪阶层白人女性的经济地位和阶级是不同的。这些小群体内部本身就极富多样性,例如在北爱尔兰的工薪阶层女性这一群体内部,她们的宗教分化就非常明显。因此,如果我们接受斯佩尔曼的观点,最终可能会导致把女性这个整体分散为单独的个体,并且没有办法可以把 ta 们连结起来。这种做法是有问题的:为了反抗女性群体普遍上受到的压迫,女性主义者们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把女性视为一个整体。扬写道,如果不这样做,“就不可能将压迫看作一个系统化、结构化、制度化的过程”(1997,17)。有些人则认为具有包容性地去定义女性群体是实现有效女性主义政治的前提,而且有大量旨在将女性归类为群体或集体的文献资料涌现出来(例如,Alcoff 2006;Ásta 2011;Frye 1996;2011;Haslanger 2000b;Heyes 2000;Stoljar 1995,2011;Young 1997;Zack 2005)。阐述这样的归类方式的论点可以分为以下几种:(a)性别唯名论——否认女性之间具有任何统一的相同点,并且不接受诉诸于女性本身以外的客观因素来定义女性; (b)性别唯实论——女性之间的确有共同特征(尽管这些唯实论者的立场与第 2 节中概述的有显著不同)。下面我们将回顾一些具有影响力的性别唯名论以及性别唯实论的立场。在此之前,我们需要注意,并不是每个人都认为包容地界定性别是可能成功的,或者对于女性的定义是必须要被解决的。米可拉(Mikkola)(2016)提出,女性主义政治不必依靠克服(她所说的)“性别论战”:女性主义者们必须明确性别这个概念,并依据一套标准来确立女性的社会身份。正如她所认为的,关于“如何定义女性”的争论已经数不胜数并且盘根错节,这个问题看上去陷入了分析的僵局,几乎不可能解决。相反地,米可拉主张放弃这个难题,因为这样做并不会构成严重的政治障碍。

性别唯名论
性别化的社会连续群体
艾里斯·扬(Iris Young)认为,“除非有那些将女性视为一个社会集体的情况,否则就没必要单独强调女性主义政治的概念”(1997,13)。为了更好地理解女性这个类别,她认为妇女构成了一个系列:一种特殊的社会集体,“其成员被动地由她们的行动所围绕的对象和(或)由其他人的行动所产生的物质效果的对象化结果而统一起来”。(Young 1997,23)。连续群体与团体的不同之处在于,团体的成员自觉地认为 ta 们有共同的目标、计划、特质和自我概念,但是连续群体的成员可以追求自己个人的目的,而不必有任何共同点。艾里斯·扬认为女性并没有被一个(或多个)共同的特征或经历联系在一起,她根据斯佩尔曼的特殊性论点确定了没有这种共同特征存在(1997,13;另请参考:Frye 1996;Heyes 2000)。相反地,女性这个类别是根据有些实践惰性的现实情况或女性围绕某些事物和现实的行为生活方式来统一的(Young,1997,23–4)。例如,通勤者们可以构成一个统一的连续群体,因为 ta 们的每个人的行为都围绕着公共汽车这个实践惰性物质对象和公共交通的应用开展。同样地,女性的生活和行为也围绕着一些实践惰性物质对象,而这些实际状态使其被定义为女性,所以女性也组成了一个统一的连续群体。
艾里斯·扬指出了两大类这种实践惰性对象和现实情况。第一,与女性身体有关的现象(生理事实),在女性体内发生的生理过程(月经、怀孕、分娩)以及与这些生理过程有关的社会规则(例如关于月经的社会规则)。第二,包含性别概念的物体和行为:代词,性别的口头和视觉表现,标示性别的手工艺品和社交空间、衣服、化妆品、工具和家具。因此,由于女性的生活和行为是围绕女性身体和某些性别编码的物体进行的,所以妇女组成了一个连续群体。这个连续群体被动地连结在一起,而这种统一性“不是由被称为女性的个体产生的”(Young 1997,32)。
尽管艾里斯·扬的提议似乎是对斯佩尔曼担忧的回应,但斯通(Stone)仍然质疑这种提议是否容易受到特殊性论点的影响:毕竟根据艾里斯·扬的观点,女性是根据她们作为女性所共有的东西(她们的实践惰性现实)而被关联在一起的(Stone 2004)。
相似唯名论
娜塔莉·斯托哈尔(Natalie Stoljar)认为,除非统一女性这个类别,否则代表女性采取女性主义行动是不合理的(1995,282)。斯托哈尔也被认为女性不共享任何相同之处。这促使她支持相似性唯名论。这种观点认为,特定类型的实体之间存在某种相似性关系(有关相似性唯名主义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Armstrong 1989,39-58)。然而并非只有斯托哈尔主张用相似关系来归类女性,其他人通常根据维特根斯坦的“家庭相似”关系做出同样的主张(Alcoff 1988;Green&Radford Curry 1991;Heyes 2000;Munro 2006)。斯托哈尔更多地依赖于普莱斯(Price)的相似性唯名论,即只有当 x 足够相似于 F 的一种范式,x 才是 F 的一员(Price 1953,20)。例如,红色实体的类型由某些选定的红色范式来规定,因此只有与这些范例足够相似的实体才能算作是红色的。因此,女性这一种类(或类别)也是由某些选定的女性范式来定义的,而那些与女性范式充分相似的人才能算作女性(Stoljar 1995,284)。
斯托哈尔认为关于女性这个概念的语义上的考量说明相似性唯名论应该被应用(Stoljar 2000,28)。但是似乎不可能仅根据女性所拥有的某种单一社会特征来应用这一概念。相比之下,“女性”是一个集群概念,而我们对女性气质的归类是根据“不同个体身上具备的不同的特征排列”来选择的(Stoljar 2000,27)。具体是以下四类特征:(a)女性生理性别;(b)现象学特征:月经、女性性经历、分娩、哺乳、害怕晚上在街上行走或害怕被强奸;(c)特定角色:通常穿着女性服装、因为性别而受到压迫或从事护理工作;(d)性别归属:“自称女人,或被称为女人”(Stoljar 1995,283-4)。对于斯托哈尔而言,女性气质与多种特质和经历有关:女性主义者在历史上将其称为“性别特质”(例如社会、行为、心理特质)和那些“生理性别特质”。尽管如此,她认为由于女性这个概念适用于(至少有一些)跨性别女性,所以一个人可以是女人但在生理上不是女性(Stoljar 1995,282)。
然而,女性这个集群概念并不能直接提供定义女性这一类别的标准。相反地,这四种类别的特征帮助我们确定女性范式,从而帮助我们确定女性这一类别。首先,在这个四个特征类别之中,任何具备其中三项特征的个体将被视为该类别的范例。例如,一名自我认同为女性,并具有女性第一性征和第二性征的非裔美国人因其性别而受到压迫,另外还有一位被“当作女孩”抚养长大的欧洲白人双性人,ta 扮演着女性角色。尽管 ta 缺乏女性生理性别特征,但仍具有女性现象学特征,所以可以被视为女性范式(Storjar 1995,284)。其次,任何“足够相似于任何范式(根据普莱斯的说法,就像[范式]之间彼此相似)的人,会成为‘女性’这个相似性类别中的一员”(Stoljar 1995,284)。也就是说,界定妇女类别中成员资格的标准是,ta 与一种妇女范式足够相似。
性别新现实主义
社会从属与性别
莎莉·哈斯兰格(Sally Haslanger)在她 2012 年的书中收集的一系列文章中,提出了一种定义女性这一概念的方法,该概念在政治上很实用,它是女性主义与性别歧视作斗争的一个工具,并且表明女性是一种社会学(而非生物学)的概念。更确切地说,哈斯兰格认为,性别是一个占据从属或社会特权地位的问题。在一些文章中,哈斯兰格主张对女性这一概念进行修正性分析(2000b;2003a;2003b)。在其他地方,她表示她的分析可能不具有那样的修正性(2005;2006)。首先考虑前一个论点。用哈斯兰格自己的话来说,她的分析是改善性的:其目的是阐明哪种性别观念最能帮助女性主义者实现其合理目的,从而确定女性主义者应该使用的概念(Haslanger 2000b,33)。如今,女性主义者需要用性别术语来反抗性别歧视导致的非正义事件(Haslanger 2000b,36)。特别是,ta 们需要性别术语来识别、解释和谈论男性和女性之间持续存在的社会不平等。哈斯兰格对性别的分析基于男性和女性在生理和社会地位这两个方面的不同之处。总体而言,社会倾向于“把特权赋予具有男性身体的人”(Haslanger 2000b,38),因此,ta 们随后占据的社会地位要优于拥有女性身体的人。而这会产生持续的性别歧视。考虑到这一点,哈斯兰格规定了她如何理解性别:
S 是一名女性,当且仅当[根据定义]S 在某些方面(经济、政治、法律、社会等)被系统地强制服从,而且 S 因为具有观察到或想象出的可以证明女性生育作用的身体特征而被“标记”为接受这种待遇的目标群体。
S 是一名男性,当且仅当[根据定义] S 在某些方面(经济,政治,法律,社会等)系统化地享有特权,而且 S 因为具有男性生理特征和生育能力的,而被“标记”为接受这种待遇的目标群体。(2003a,6–7)
以下是作为男人和女人的构成要素:使 S 被称作女人的因素在于 S 因性别而被压迫;使 S 成为男人的原因在于 S 在性别上拥有特权。
哈斯兰格的修正性分析是违反直觉的,因为这种分析使没有因为性别原因受到压迫的女性不能被算作女性。比方说,英国女王没有因为性别原因而受到压迫,因此按照哈斯兰格的定义,她不能被算作女性。同样的,所有没有性别特权的男性也不算男人。这表明哈斯兰格的分析方法不应该被采纳,因为它没有捕捉到语言使用者们在使用性别术语时的真实想法。但是,哈斯兰格认为这不是拒绝这些定义的理由,她认为这些定义是修正性的:它们并不是为了去识别我们直观上的的性别术语。作为回应,米可拉(2009)认为,像哈斯兰格那样的对于性别概念进行的修正性分析在政治上无益,而且在哲学上无需。
还要注意的是,哈斯兰格的建议是消除主义的:性别公正将根除性别区分,因为它将废除那些导致性别压迫和特权的社会结构。如果停止性别压迫,社会男女性别的概念将不复存在(尽管仍然会有生理性别男和生理性别女)。但是,并非所有女性主义者都赞成这种消除主义的观点。斯通认为,哈斯兰格没有留出任何空间来积极地重新评估女性的形象:因为哈斯兰格用从属地位来定义女性,
任何挑战其从属地位的女性其实都从定义上讲在挑战其作为妇女的身份,即使她没有打算……积极改变我们的性别规范,以及摆脱(必要的)女性性别的从属地位。(Stone 2007,160)
但斯通认为以上说法不仅是我们不希望的——女性应该能够去挑战她的从属地位而同时保留女性的身份。而且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因为女性气质的规范可以被不断修改,所以女性可以作为女性而不因此处于从属地位”(Stone 2007,162;米可拉[2016]也认为,哈斯兰格的消除主义是不可取的)。
西奥多·巴赫(Theodore Bach)也认为哈斯兰格的消除主义是不可取的。但是,他认为哈斯兰格的立场面临着另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女性主义面临以下困扰(相比之下):
代表性问题:“如果没有真正的‘女性’群体,那么代表女性这个整体提出道德主张和推进政治政策就是不合理的”(Bach 2012,234)。
共同性问题:(1)不存在所有妇女在跨文化和跨历史背景下拥有的共同特点。(2)利用一些非常重要的特质来界定女性的社会地位,使拥有这些特质的人享有特权,而不拥有这些特质的人则被边缘化(Bach 2012,235)。
根据巴赫的说法,哈斯兰格解决这些问题的策略是“社会客观主义”。首先,我们根据“适当的抽象关系属性”来定义女性(Bach 2012,236),这可以避免共同性问题。其次,哈斯兰格采用了“客观性的本体论上的狭义概念”(Bach 2012,236)来回应了代表性问题。巴赫认为哈斯兰格的解决方法具体来说就是主张女性构成了一种客观的类型,因为女性们在客观上是彼此相似的,而并非简单地根据我们的背景方案把 ta 们归类在一起。巴赫指出哈斯兰格的说法不够客观,我们应该基于政治理由“提供一种更有力的本体论性别归类,而这种归类方式能区分出男性和女性的自然属性,同时 ta 们具有可以被解释的本质性特征”(Bach 2012,238)。因此,他提出女性是一种自然的、具有历史重要性的类别:
女性的基本属性是参与到女性的世系中去,一个人满足这一点则可被称为是“女性”中的一员。为了体现这种关系属性,一位女性必须是祖先女性的后代,在这种情况下,她必须经历了历史上性别系统复制女性的本体遗传过程。(Bach 2012,271)
简而言之,判断一个人女性身份的依据不是与其他女性共有的浅显特征(如占有从属的社会地位)。相反,一个人之所以是女性,是因为 ta 拥有特定的经历:ta 经历了无处不在的性别社会化的本体遗传过程。用这种方式思考性别问题,比哈斯兰格的简单地呼吁共同的浅显属性,提供了一种更强的统一性。
然而,巴赫的观点具有反对跨性别的暗示。毕竟,在他看来,未经历过女性社会化过程的跨性别女性将不能被算作女性(Mikkola [2016]详细阐述了这个见解)。更令人担忧的是,跨性别女性将会被视为男人,而这与 ta 们的自我身份认同相反。贝特彻(Bettcher)(2013)和詹金斯(Jenkins)(2016)都考虑了性别自我认同的重要性。贝特彻认为,不仅仅只有一种“正确”的方法去理解女性身份:最起码有比较普遍的(主流)概念和反叛式的(跨性别)概念。像巴赫这样的主流观点往往会抹杀跨性别者的经历,并在女性主义运动中将跨性别女性边缘化。与其让跨性别女性必须为其自我认同进行辩护,不如从一开始就承认她们的自我认同。因此,贝特彻认为:“在分析‘女性’等术语的含义时,不应该忽略在跨性别亚文化中使用这些术语的替代方式;这些术语的用法需要作为分析的一部分加以考虑”(2013,235)。
在此之上,詹金斯(2016)讨论了哈斯兰格的修正主义方法如何不恰当地将一些跨性别女性排除在女性这个社会种类之外。在詹金斯看来,哈斯兰格的修正性方法论实际上产生了不止一个令人满意的目标概念:一是“与哈斯兰格提出的概念相对应,并把性别当作一种强加的社会阶级”;二是“把性别当作一种生活化的身份认同”(Jenkins 2016,397)。后者使我们能够将跨性别女性纳入女性的社会类别,而按照哈斯兰格的性别社会阶级论,这些跨性别女性将被不恰当地排除在外。
除了她的修正性论点,哈斯兰格还提出她对女性的修正性分析可能不像最初看起来的那样具有修正性(2005,2006)。语言使用者虽然成功地进行了参考修复,但普通的语言使用者们并不一定能准确地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们对语言的使用可能会被压迫性的意识形态所歪曲,它会“使我们被自己的思想所误导”(Haslanger 2005,12)。尽管她的性别术语并不直观,但这可能仅仅是因为压迫性的意识形态误导了我们对性别术语的理解。我们日常的性别术语可能表示与我们认为的含义完全不同的东西;而我们可能对此一无所知。那么,也许哈斯兰格的分析已经包括了我们的日常性别词汇,向我们揭示了我们实际使用的术语:无论是我们是否刻意为之,我们在日常中使用“女性”这个词时可能都基于性别的从属地位。如果是这样的话,哈斯兰格的性别术语就不是彻底的修正主义。
索尔(Saul)(2006)指出,尽管我们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基于社会从属地位使用了“女性”这个词,但同时也很难证明是这种情况。这需要证明我们实际上使用的性别术语是哈斯兰格提出的性别术语。但是,要找到我们应用日常性别用语的准确依据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们的使用方式各不相同而且千奇百怪(Saul 2006,129)。因此,哈斯兰格需要做更多工作,以证明她的分析是非修正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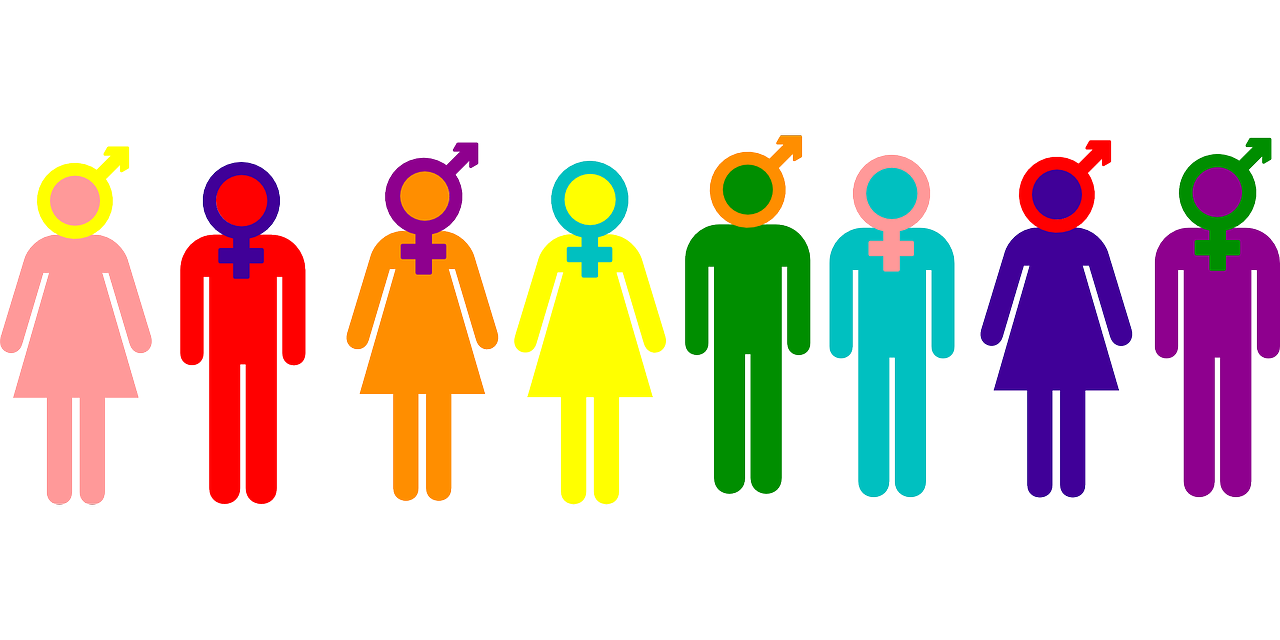
性别的统一本质主义
夏洛特·维特(Charlotte Witt,2011a;2011b)主张一种特殊的性别本质主义,维特称其为“统一本质主义”。她的动机和出发点如下:许多普通人报告说性别对 ta 们来说至关重要,并声称如果 ta 们具有不同的性别,ta 们将是一个不同的人。统一本质主义试图理解和阐明这一点。但是,维特的工作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与第 2 节讨论的早期(所谓的)本质主义者或性别现实主义者的立场截然不同:维特并没有假定上文讨论的女性的某种基本属性,因为这种基本属性没有考虑到女性个体间的差异。此外,统一本质主义与那些为了回应如何看待妇女的社会种类问题而形成的立场大不相同。它不是要解决性别唯名论者和性别唯实论者之间的典型争论,也不是要为女性主义政治团结提供理论基础而阐明某种所谓的把妇女团结在一起的共有特质。相反,统一本质主义的目标是使人们普遍认为性别是自我的构成要素。
统一本质主义是一种个人的本质主义。传统上,哲学家们把种类本质主义和个体本质主义区分开来:前者考察的是把某一种类的成员联系在一起的是什么,或者说在这一种类的所有成员中,ta 们都具有什么共同的特质。后者问:是什么使一个人成为这个人本身。我们可以进一步区分两种个人本质主义:克里普克的身份本质主义和亚里士多德的统一本质主义。前者问:是什么使一个人成为这个人?然而,后者提出了一个稍微不同的问题:是什么解释了个体的统一性?是什么解释了单个实体的存在高于其构成部分的总和?(女性主义者关于性别唯名论和性别唯实论的常见争论,主要是关于种类本质主义。关于个人本质主义,维特的统一本质主义与这些常见争论截然不同。)在两种个人本质主义中,维特认可亚里士多德的统一本质主义。根据这种观点,某些功能性要素具有一种统一的作用:这些要素使物质的各个部分构成了一个新的个体,而不仅仅是一堆东西或粒子的集合。维特以房子为例:房子的基本功能属性(这个实体是干什么用的,它的目的是什么)将房子的不同构成部分统一起来,这样就有了房子,而不仅仅是构成房子的粒子的集合(2011a,6)。性别(作为女性/男性)也是相似的道理,它提供了“规范性的统一原则”来组织、统一并决定社会中个体的角色(Witt 2011a,73)。因此,性别是构成社会个体的统一本质要素。
理解维特采用的性别与社会个体的概念非常重要。首先,性别是一种社会地位,它“围绕者生育功能……女性受孕和生产,……以及男性生育功能”(Witt 2011a,40)。这些是女性和男性的社会传导的生殖功能(Witt 2011a,29),它们不同于生理上的生殖功能,后者大致上对应标准的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区分中的生理性别。维特写道:“作为女性就是认识到自己有一种独特的的生育功能,而作为男性就是认识到自己有另一种不同的生育功能”(2011a,39)。其次,维特区分了个人(具有自我意识的人),人类(生物学上的人)和社会个体(同步和历时地占据社会职位的人)。这些本体论类别是不平等的,因为它们具有不同的持久性和身份条件。社会个体受社会规范的约束,而人类受生物学规范的约束。这些规范在两个方面有所不同:首先,不同文化的社会规范不同,而生物学规范是跨地域普遍存在的。其次,与生物学规范不同,社会规范要求“他人承认此人既对社会规范做出响应,又可以根据社会规范被评估”(Witt 2011a,19)。因此,成为一个社会个体并不等同于成为一个人类。进一步说,维特用内在心理状态和自我意识来定义自我人格。但是,社会个体性是根据占据社会地位的外在特征来定义的,而这取决于社会世界的存在。因此,这两者并不等同:人格本质上是关于内在特征的,即使没有社会世界它也会存在,而社会个体性本质上是在没有社会世界的情况下就不可能存在的外在特征。
维特的性别本质论观点与社会个体紧密相连,而非与个人或人类有关:或者说将个人或人类进行性别划分是一个类别上的错误。但是,为什么性别对于社会个体至关重要?对于维特来说,社会个体是指那些在社会现实中拥有社会职位的人。此外,“社会职位具有与之相关的规范或社会角色;一个社会角色是指占据特定社会地位的个人在特定社会地位下的反应和受到的评价标准”(Witt 2011a,59)。但是,对于一个社会个体来说,我们同一时间或在不同的时间处于多个社会职位:我们可以是女性、母亲、移民、姐妹、学者、妻子、社区组织者和团队运动教练。现在,维特的问题是如何统一这些职位,从而构成一个社会个体。毕竟,一连串的社会职位并不能定义一个人(就像一堆性质,比如白色,立方体形和甜美的属性并不能完全定义方糖)。对于维特来说,性别(女性或男性)承担了这种统一的角色:
性别是一种普遍和基本的社会职位,它统一并决定了所有其他社会职位的同步性和历时性。它不是通过物理上的方式将它们统一起来的,而是通过提供规范的原则来统一它们。(2011a,19–20)
维特所说的“规范性统一”指的是:鉴于我们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职位,我们对各种社会规范都会有所反应。这些规范是“复杂的行为和实践模式,它们构成了一个人在特定的社会职位和社会环境下应该做的事情”(Witt 2011a,82)。这套准则可能会冲突:作为母亲的准则规范可能(并且确实)与作为学术哲学家的准则规范发生冲突。然而,为了使这种冲突存在,规范必须对单个社会个体具有约束力。那么维特问:是什么解释了受冲突的社会规范约束的社会个体的存在和统一性?答案是性别。
性别不仅仅是统一社会个体的社会角色。维特认为它是统一社会主体的大型社会角色。首先,如果性别满足两个条件(维特声称它确实满足),则它是一种大型社会角色:(1)它是否提供了社会个体共时和历时统一的原则,以及(2)是否改变并定义了范围更广的其他社会角色。在通常情况下,性别满足了第一种情况:社会个体的性别化社会职位会在 ta 有生之年持续存在。此外,维特还坚持认为,跨性别人士并不是这一主张的反例:转型意味着旧的社会个体已经不复存在,而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个体。而这与同一人坚持并通过转型的方式经历社会个体的变化是一致的。性别也满足第二个条件。它会影响其他社会角色,例如成为父母或专业人士。社会对这些角色的期望因主体的性别而异,这是因为性别强加了不同的社会规范来控制其他社会角色的执行。现在,相对于其他一些社会类别,比如种族,性别不仅仅是一个大型社会角色,它是具有统一性的大型社会角色。无论在是跨文化还是跨历史的考虑下,这种观点都成立。维特声称父权制是一种社会普遍性(2011a,98)。相比之下,种族分类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文化中是不同的,而且种族压迫并不是人类文化的普遍特征。因此,性别是对于一个社会个体来说是一个更重要的社会角色。这种对性别本质主义的论述不仅解释了社会行为者与其性别的联系,而且还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式来考虑女性主体——这是女性主义政治的核心。
性别作为一种地位
琳达·阿尔科夫认为女性主义面临着身份认同危机:女性的范畴是女性主义的出发点,但是关于性别的各种批判粉碎了这种类别,而且女性主义者也不清楚作为一名女性意味着什么(2006 年,第 5 章)。作为回应,阿尔科夫将性别定位为“地位”,从而“性别是一个人占据的地位,并且可以从中扮演政治角色”(2006,148)。具体来说,她用社会地位来促进特定的性别身份(或自我观念)的发展:“女性的主体性(或作为女性的主观体验)和女性的身份就是由女性的地位构成的”(Alcoff 2006,148)。阿尔科夫认为,基于(实际或预期的)生殖角色来区分个体是有客观依据的:
女性和男性的区别在于其与生物生殖的可能性关系不同,生物生殖指的是涉及到人体的受孕,分娩和母乳喂养。(Alcoff 2006,172)
这种想法是,那些被生物学标准归类的女性,尽管她们可能实际上不能生育,但与那些被标准归类为男性的人相比,她们会受到“一套不同的关于生育的习俗、期望和感受”。(Alcoff 2006,172)。此外,这种与生育可能性的不同关系被用作许多定位女性和男性的文化和社会现象的基础:
它是各种社会隔离的基础,它可以体现人一生中经历的不同发展形势,它可以产生各种不同的情感反应,比如骄傲、喜悦、羞愧、内疚、遗憾,或因成功避孕而产生的极大的解脱。(Alcoff 2006,172)
因此,生殖是区分个体的客观基础,它具有文化层面上的差异性,因为它对女性和男性的定位是不同的:一个人的身体类型不同,ta 的生活经验也会不同。这就促进了性别社会身份的建构:一个人在生殖中的作用有助于确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这限制了特定性别社会身份的发展。
由于妇女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因此,“并不存在所有妇女共同拥有的性别本质”(Alcoff 2006,147-8)。尽管如此,阿尔科夫承认她的说法与 1960 年代最初的生理性别/社会性别理论相似,因为性别差异(根据生殖劳动的客观划分理解)为某些文化安排(性别化社会身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不过事后看来,
“我们可以看到保持性别认同的客观类型与文化上多样的性别习俗之间的区别,这并不意味着在文化和统一性之间有一种绝对的老式的区分。”(Alcoff 2006,175)
也就是说,她的观点避免了生理性别只与自然界有关,而社会性别只与文化有关的荒谬说法。相反地,基于生育可能性的区分是由这些可能性所产生的各种文化和社会现象(如各种社会隔离)所决定和影响的。例如,技术干预可以改变性别差异,由此证明以上说法(Alcoff 2006,175)。女性特定的性别化社会身份是由其依存的环境立场所构成的,这就为女性政治提供了出发点。
结论
这篇文章首先关注了反对生理决定论的女性主义论点,以及性别是社会建构的主张。接下来,我们研究了女性主义者针对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普遍理解的批评,以及其区别本身。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在最后部分探讨了如何为女性主义政治目的确定统一的女性类别,并阐述了(至少)两个观点。首先,性别——或者说如何区分女性和男性——仍然是一个现实问题。其次,女性主义者没有完全摒弃性别取决于社会因素的观点,并且(在某种意义上)生理性别与生物性别是不同的。对于性别的最佳、最有用或(甚至)正确的定义我们仍然没有定论。此外,一些当代女性主义者仍然认为 1960 年代初的社会性别/生理性别理论具有价值。
致谢
我非常感谢 Tuukka Asplund,Jenny Saul,Alison Stone 和 Nancy Tuana 在撰写本文时提供了非常有益和详尽的评论。
(全文完)